饭包,是旗人的另一特色食品。所谓“饭包”,一开始就是用白菜叶子包上米饭吃,是满洲人最普通的吃食。行军打仗,放牧狩猎,都离不开它。
清朝建立,天下平定,旗人吃饭包,一是出于民族习惯,二是本着忆苦思甜,不忘马上得天下。但到清中叶乾嘉年间,饭包的内容不断丰富起来,以至于脱胎换骨,成了一种十分讲究的上等食品。饭包里米饭退居二线,主角逐渐为各色干果、鸡鸭肉所代替,更有钱的旗人还把各种野味,如野鸡肉、野鸭肉等放进饭包,小小的饭包开始包容越来越多的美食内容,达到全盛。清末民初,旗人生活走向困苦,饭包又回到清初的状态。旗人的饭包从米加白菜,到加入鱼、肉,到加入野味,到内容越来越少,越来越简单,可以由此透视出清代旗人生活的轨迹,折射出旗人复杂的民族心态和饮食心态。
史书记载,旗人入关前的饮食十分简朴,“面食酒醪,皆和以酪”,肉和奶一直是当家食品。
当然,对于几乎日有所战的旗人来说,现实的生活条件也不可能让他们耗时费工地讲究吃喝。各部族之间战事一起,士兵们的常备战饭是随身携带的马奶和炒面。在双方偃旗息鼓暂罢刀兵的间隙,士兵们就从马背上解下装炒面的皮囊,就着马奶,用手抓着炒面吃。真可谓风餐露宿,饱受艰辛。
这种炒面多是用高粱米磨成的面粉所制,东北地区俗称“秫米面”。做法是先把高梁碾去糠皮,再用细磨磨成面粉,用油炒成。这样既便于随身携带,又可以防止粮食馊腐变质,是行军打仗必不可少的军粮。据说老北京人喜食的油茶,就是从这种用作军粮的油炒面演化而来。北京的油茶是用白面作原料,油分为香油和牛骨髓油两种,风味各有不同,吃时外撤核桃仁、熟芝麻、绵白糖和糖桂花。
“饽饽”一词,始于元代。世祖忽必烈改金中都为元大都,大批蒙古族人随之入京。蒙、汉人民杂居相处,风俗渐近,大都市面上开始出现以蒙古饽饽为主的民族食品。到了清代,糕点已成为北京城的名吃特产,蒙古饽饽之外,又出现了满洲饽饽。老北京的旗人不仅把糕点称作“饽饽”,把水饺称为“煮饽饽”,还把烤烙的面墩叫“硬面饽饽”、“墩饽饽”。北京城的汉民们把蒙、满饽饽又叫“达子饽饽”。据说过去北京城讲究的老字号饽饽铺必须在门外悬挂的漆金木牌上用汉、满、蒙三种文字书写,缺一不可,以示其正规。
据老舍夫人胡絜青先生说,把糕点不叫点心,而叫饽饽,在老北京有这么个讲究:原来,清代在给死刑犯施刑时也按罪过分为数等,有赐自缢、斩立决、剐刑等处决方法。其中剐刑也叫凌迟,最为残酷。刽子手要对犯人千刀万剐,直至气绝身亡,犯人死前痛苦万分。有些犯人亲属怕自家亲人受不了这种酷刑,就用重金贿赂行刑者,让他们在对犯人行刑时,先一刀结果了犯人的性命,使其免受一刀一刀零刺的碎身之苦,而人的致命之处莫过于心脏。于是刽子手就把这扎向犯人心脏的头一刀叫作“点心”。所以那时候,大伙儿都忌讳“点心”这两个字,不光去糕点铺买点心说成是买饽饽,就连满街的糕点铺门前店内也没有写着“点心”二字的幌子招牌,都一律称作饽饽铺。
清道光以前,北京城的糕点业称为“糖饼行”,道光以后,才改称叫“烘炉”。早年老北京的糖饼行分南、北两案,南案由江浙商人经营,专做南味糕点;北案由京畿、直隶商人组成,制售京式糕点。回回糕点商在京开设的清真糕点铺,亦属北案。清代糕点在此基础上,又加入“满洲饽饽”。“满洲饽饽”并非是旗人进京后才有的,早在明代,他们便开始大面积种植粘秫米、江米、糜子等粮食作物,为打制糕点准备了原料。用这些杂粮制成的“饽饽”有淋蒸糕、苏叶饽饽、打糕、洒糕、盆糕、搓条饽饽等,其中打糕和朝鲜族的打糕如同孪生。搓条饽饽在满人入关后,参照了汉族“芙蓉糕”的制作工艺,加以改进,制成了满式名点——萨其马。
在老北京的各式糕点中,“满洲饽饽”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清道光二十八年所立《马神庙糖饼行行规碑》中规定,满洲饽饽是“国家供享、神祇、祭祀、宗庙及内廷殿试、外藩筵宴,又如佛前供素,乃旗民僧道所必用。喜筵桌张,凡冠婚丧祭而不可无,其用亦大矣!”
碑文中有“喜筵桌张”一语,“桌张”,即饽饽桌子,“旧时旗礼,一切婚丧大事,俱有桌张,今渐无矣。”(清末得硕亭语)饽饽桌子是老北京满洲饽饽铺的大宗买卖,齐如山先生曾撰文介绍过它的制法:“下面用一长约三尺左右,宽约二尺左右,高约尺余之木桌,上摆铜盘十个。每盘饽饽20块分四罗(此种饽饽之名曰点子,亦满洲语之名词),共200块一层,摆好上压以红漆木板,板上再照样摆铜盘及饽饽,如此摆至三层即妥。再高则五层、七层可至20层,然九层亦算很讲究矣。无论几层,顶上须单摆纸花或鲜花、或水果一层方算完备。从前九层之桌合价不过十余元,饽饽之味颇甘美。近则几需5000余元,而饽饽则几不可食矣。闻各王圆寂祭祀所用之饽饽,皆系木质所作。每次用时取出摆好,事完即又藏之,也算省事。”(详见《故都三百六十行》)
旗人送饽饽桌子,讲究送得越多、摆得越高,越显出对主家的敬重,于是竞相攀比,令饽饽铺坐收渔翁之利。清末北京满洲饽饽铺最大的几宗生意,还要数当年皇姥姥(即慈禧生母)、光绪的生父醇亲王奕譞及福晋、恭亲王奕?及福晋等人的丧葬祭奠。当时京城内外文武官场,无不恭送饽饽桌子,每处都有数千桌乃至数万桌,丧家哪里放得下?承办丧礼的管家只能以虚数相报,饽饽铺却仍照数收银,两下勾结,自然也不会亏待了管事的人。为此,东四牌楼南及地安门外各大饽饽铺无不大大地发了一笔横财。只是因为国势衰微,好讲排场的旗人渐渐无力支撑门面,送饽饽桌子的自然少了,满洲饽饽铺开始改变经营方向,发展满制汉点。
所谓满制汉点,是说饽饽铺采用满点的制作工艺,做出的各式汉族糕点,主要是为了适应旗人久居京城,饮食习俗逐渐汉化的需要。比如花糕中掺与奶皮,即为奶皮花糕;元宵的馅中掺入了奶皮,即为奶皮元宵;糯米用鲜奶浸后包粽,唤作奶子粽;月饼的馅中拌入了奶皮,就成了奶皮月饼。说起满式月饼,当首推宫中内膳房所做的宫廷月饼,是集苏式、广式、京式三种传统月饼制作工艺于一身的“贵族”月饼。宫廷月饼在皮上压有云彩、蟾宫、桂树、玉兔等吉祥图案,还上有各种颜色,有彩绘的、红边白心的、白边红心的。全红的称“自来红”,全白的称“自来白”。“自来红”和“自来白”都是酥皮月饼,香油和面,有彩绘图案的则属于提浆月饼。据档案记载,提浆月饼上色用的颜色分为飞金、银砂、大绿、石青、彩黄、靛粉、广胶、苏木。宫廷月饼中最大的直径有55厘米,重十斤;最小的月饼仅重一两五钱,此外,还有重三两、重五两、重一斤、重三斤等多种规格。其中十斤重和三斤重的大月饼主要用于摆桌祭祀,在十斤重的大月饼上印有“郁仪宫”字样和玉兔捣药图案,祭祀已毕,这块大月饼又被精心包装起来,贮存到当年的除夕,再由帝后皇子公主们分而食之。至于三斤重的大月饼则于中秋夜祭祀后切成数块,连同各式小月饼、“莲花团圆瓜”、鲜果等分赐妃嫔、朝中大臣、内监和宫女诸人。
老北京的各式糕点,在用油上就有所区分,满洲饽饽铺擅使奶油,汉族糕点铺则多用大油,清真糕点铺喜用香油,这样做出的特色糕点自然风味不同。
老北京旗人每逢婚丧喜寿诸事,都到满洲饽饽铺买糕点。铺里常年备有“无馅以面和糖为之”的印面饽饽、“送寿礼用之”的寿意饽饽、叠落如“宝塔”的层台饽饽等。
旗人用于祭祖供佛的满式糕点是蜜供。蜜供就是用搓条饽饽搭起的外实内虚的大罩子,形状各异,大小不一。有万字供、十字供、扇面供、银锭供、圆形供和“宝塔”供诸种花样儿,其中万字供最为精细。每座为一碗,五碗为一堂,高者三尺,低者只有五寸许。加红丝的供神佛,叫“红供”;不加红丝的用来祭祖,叫“白供”。
清末民初,北京城的糕点供品首推位于朝阳门外坛口的永兴斋饽饽铺,专做满洲饽饽。永兴斋始创于清光绪六年(1890年),到1955年公私合营,经营60多年不衰。永兴斋的开业东家叫王芝亭,是个汉人,早年在京城第一大饽饽铺“毓盛斋”学徒,制售满式糕点是他的绝活。永兴斋的糕点一律自产自销,生产工艺十分严格:面粉始终用当时西直门外的元顺成粮栈和它的几个联号元顺兴、元顺常、元顺功、元顺永等几家油盐粮店的货,即所谓“元”字号的“重箩细面”;冰糖用当时最好的“石里冰”,又称“闽糖”;白糖用“本港”白糖,由前门外“义”记糖庄进货;油从“裕盛公”白油局子进货;木炭则从京西山区用骆驼往回驮……如此精心的选料,其所制糕点的质量可想而知。永兴斋还不断求新,研制出不少精制的糕点,如芙蓉奶油萨其马、七宝缸炉、八珍糕、奶油棋子桂花劳脯、卧果花糕、金线小油糕、蜜饯上品细小饽饽(仅此一项就有40多个花样),至于宫廷糕点,其生产品种不下千种。
据永兴斋饽饽铺的少东家王君稷回忆:“王芝亭与工部陈姓尚书是世交(王芝亭的祖上曾任太医院堂官),与李莲英也是朋友,因而内务府所辖饽饽房每年都指派永兴斋制作大量传供。永兴斋红炉局每个月起码要用半个月的时间做传供,然后才能做门市上的糕点。做传供的原料均由内务府提供。做时由掌案亲自动手,一年四季需分别做出不同的花色品种。”
“永兴斋每年还给恭王府、惇王府、醇王府、弘王府及中堂府制作饽饽,这也和给宫廷做传供一样,各王府不仅发给数目可观的加工费,还另外有赏钱。……永兴斋除承做宫廷、王府的传供之外,另一项重要收入就是为各寺庙制作供品。如朝外东岳庙、南海慧寺、关帝庙等处的全年供品,都是从永兴斋购买。此外,和平门的吕祖阁、德胜门的拈花寺、琉璃厂的延寿寺、东便门的蟠桃宫、地安门的火神庙和京西檀柘山的岫云寺等等寺庙的供品,一部分也由永兴斋承做。”(详见《永兴斋饽饽铺》)
其实,永兴斋门市上的生意也很兴隆,能占到总销售量的一半以上。过去,京东八县的农民都到永兴斋买供品,1925年冬天,一连半个多月都是阴雪天气,家家摆供,谁知几场大雪过后,东郊农民发现朝外另一家饽饽铺“毓顺斋”的蜜供由于糖炒得嫩都塌架了,而永兴斋的蜜供却一点没变样儿。此事一经传扬出去,永兴斋的名气更大了。
饽饽(糕点)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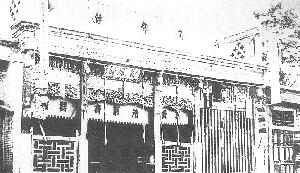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