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称为北京史的巨擘,如果没有他,人们恐怕难以像今天这样明白北京的历史;他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拓者之一,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将他誉为中国最富有激情的地理学家。
他是最早接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中国人,如果少了他的敏锐和果敢,我们或许还要在“申遗”的路上徘徊更久。
当我国目前已经入选的33项世界遗产的光芒闪耀于天地之间时,当更多的文化遗产因获得有力的保护而转危为安时,一个名字值得记忆与敬重,那就是侯仁之老人。
2013年10月22日下午2时许,这位被称为“活北京”的老人,永远离开了北京——这座他毕生爱着的城市。再过一个多月,就是他102岁的生日了……

侯仁之作报告讲北京历史地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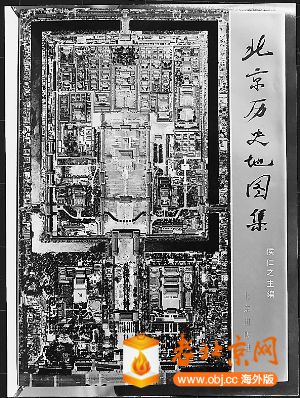
《北京历史地图集》

侯仁之和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弟弟在清华气象台前。
102岁的侯仁之是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学科创始人,还是将世界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一个青年能在30岁以前抓住他值得献身的事业,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国家和社会都要因此而蒙受他的利益。”他在33岁时所说的这番感言,更像是对自己一生的预言。 1 “我们不了解昨天和前天, 怎能更好地了解今天呢?” 曾经在北京的西二环路东侧,经常能看到侯仁之老人坐在轮椅上,注视着身旁呼啸的车流。在他身下4米,是800多年前金中都皇宫雄伟的大安殿遗址,而他前方的大道,正穿过这片古代宫城的中央。 他倔强地站起身来,手持拐杖轻走几步。此时,天雨飘散,洗净了周围一片葱绿。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的北京所历经的沧海桑田,在这一刻得到了最为真实的诠释。 这是在北京广安门附近的滨河公园,这片土地,老人过去曾多次探访。后来,他行走不便了,仍情系于此,再来看看一直是他的期盼。 “那是在1984年,我正在美国讲学,听到北京正准备在西二环路建设滨河公园,特别高兴,就写了一篇文章寄回来,发表在《北京日报》上。”侯仁之边走边说,“我在文章里提出,建这个公园非常重要,因为它正位于金中都宫殿群,这段历史应该让人们知道。” 他的建议得到了重视,后来在公园内立了一块碑,上面是他写的《北京建城记》。 1990年,在北京西二环路施工中,在公园及道路地下4米处发现一处大型夯土遗址,经考证,这正是金中都皇宫的主体建筑大安殿,而沿这处遗址的南北一线,还找到了金中都宫城大安门等12处。湮没已久的金中都宫殿群,终于得到科学而清晰的实证。 “金中都是北京城在历史上作为封建王朝统治中心的开始。元灭金之后,做出放弃中都的决定,并于东北郊另建新城,这就是著名的元大都,也是今天北京明清古城的前身。”侯仁之讲述道:“搞清楚这段历史是十分重要的,不懂城市的历史怎能爱我们的城?不爱我们的城怎能爱我们的国?” 在滨河公园以西数百米,隔着二环路与几幢塔楼,有一个被建筑工地包围的干涸水池,这是金中都宫城的唯一遗存——鱼藻池遗址。老人来到这里,寻找9年前他写下的碑文。可是,碑已不知去向,似乎已伴随着远逝的历史而踪迹全无。老人显得有些伤感,但他得知,北京市有关方面已在考虑整治恢复此处遗址的计划,几分欣慰之情又浮在脸上。这复杂的情感,似乎是历史工作者所无法摆脱的。 他还记得1934年他在燕京大学读历史系时听到的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与林徽因关于北京古城的论述:“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他正是被这诗与画的语言所深深触动,才走进了北京的历史长河。 在北纬40度上下的世界各大城市里,北京城是最长寿的,今天她仍保持着旺盛的活力。侯仁之倾其一生,探解着这个古老城市的生命源泉。“我们不了解昨天和前天,怎能更好地了解今天呢?”侯仁之如是说。 2 “期待我所从事的‘冷’学科后继有人” 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现代化建设问题讨论会上,被誉为“北京史巨擘”的侯仁之指出:“深入揭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性质和特点,是进行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可以说,侯仁之几乎将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北京城。“经世致用”或谓“用世益民”是侯老科学研究的真谛。1965年他便主持完成了一项有关北京城地下埋藏古河道的研究,这对排除城市建设中的隐患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致力于为首都建设服务,对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城市建设包括天安门广场等重要设施的建设都做出过重要贡献,解决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的特点及其客观规律等关键性问题,有助于推进北京旧城的改造、城市的总体规划及建设等工作。 北京修建西站,最初选址时曾考虑利用莲花池,因为池水几近干枯,便于地下建筑,并且没有居民搬迁的问题,可以很快动工。但侯仁之认为:莲花池这个地方很重要,追根溯源,它和北京城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据史料记载,北京城有3000多年的历史,起源于蓟城,它最早的生命来源——水源,就是莲花池。“一个人,绝不可以忘记自己的过去,一个如北京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也绝对不可以忘记自己的起源。”侯仁之反复建议将莲花池保留下来。最后,市政府决定保留莲花池,在莲花池东北岸将西站建设起来,成为首都的又一新大门。此后,北京进行中心区水系治理工程,侯仁之又以极大的热情呼吁恢复莲花池昔日“绿水澄澹,川亭望远”的景观,使富有历史渊源的风光出现在京门一侧。 历史上的北京城,其平面布局匀称而明朗,设计规划美轮美奂,达到了封建王朝文化、艺术和建筑的顶峰。北京的城市规划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从北到南的中轴线。在封建王朝时代,城市的中轴线只向南发展,宫殿也一律面向正南。这是因为黄河流域是典型的季风气候,冬季受到强烈的西北风的影响,因此主要建筑一律面向正南,在这个传统的意识形态里产生了“面南而王”的思想,历代封建统治者一定面对正南统治天下,都城设计的中轴线也一直向正南发展。侯仁之这位当年燕园的长跑冠军,曾徒步考察过北京的山系,并冒着倾盆大雨察看北京城水系的来龙去脉。他揭示和论证了北京城的起源和变迁,提出了北京城市史上的三个里程碑:新中国成立前以紫禁城为中心的“帝王至上”的封建国都;新中国成立后以天安门广场改造为代表的“人民至上”的新首都;20世纪80年代后期又以亚运会开辟中轴路向北延伸,体现了“和平、友谊、进步”的主题、向世界敞开胸襟的新思想。“北京的老城有一条中轴线,现在,在这条线上有两个明显的标志性建筑。一个是紫禁城,已经列入了世界公认的优秀的历史文化建筑。一个是天安门广场,它已经由原来的宫廷广场最终变成了人民广场,代表着我们国家正在蓬勃发展……过去的北京一直向南发展,封建统治王朝的时候,明朝建立现代的北京城,先建内城,后建外城,天坛,先农坛,所以这个轴线是向南的。后来,亚运会决定要在中国召开,于是决定向正北发展,所以把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放在正北方,它在北辰路北,为什么,北辰就像北斗星一样。北京亚运会后,为迎接2008年的奥运会又进一步向北发展,在北中轴线正北又建立了奥林匹克体育公园,从亚运会再到奥运会,向北发展,这标志着中国开始走向国际,走向世界,走向了新时代。”这样北京城的象征意义实在是太重要了,任何国家都没有。每每谈到中轴线上的这些变化,侯仁之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被誉为“活北京”的侯仁之,从现代地理学的角度,揭示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的特点及其客观规律等关键性问题,其学术价值超越了地理科学的范围,成为北京旧城改造、城市总体规划及建设的重要参考。除了将自己渊博的学识应用到北京城市的实际建设中,对于介绍北京的历史,宣传保护北京旧城风貌的意义,激发人们热爱北京的情感,侯仁之从来都是乐而为之的。而一旦发现影响、破坏文物古迹的现象,他就会感到痛心疾首,并且要不遗余力地大声疾呼,设法制止。正是在他的积极努力下,长期保护不善的卢沟桥才有了今天的模样。他还十分看重北京城的水系建设,正是在他的倡议下,干枯的莲花池得以碧波荡漾,废旧的后门桥得以清水环绕。 在历史地理学、历史考古学和城市建设学等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的侯仁之,早在1950年发表的《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中,就第一次从理论上阐明了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的区别及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和任务。他倾注毕生心血在理论和方法上发展了现代历史地理学,开创了城市历史地理和沙漠历史地理研究的新领域,系统地揭示了几个类型的城市发展的规律特点及其地理条件,为有关的城市规划做出了贡献,并培养了我国第一代历史地理学研究生、博士生。面对诸多荣誉,老人的反应很平静:“我只希望对我的这些奖励,能够引起人们对历史地理学的关注。学问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这是以有涯逐无涯的一个无穷尽的过程。我们要用自己的学问,以使人类的发展臻于尽善尽美的地步。现在我经常想到一句话是,‘老牛自知黄昏晚,不待扬鞭自奋蹄。’我当努力奋发,继续前进,但是更期待着我所从事的‘冷’学科后继有人。” 3 中国“申遗”第一人 1980年的春天,“文革”的阴霾渐渐散去,中国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从沉寂走向昂然。就在这个春天,侯仁之接受了美国和加拿大几所学校的讲学邀请。距离上次漂洋过海去异国求学,已经20多年过去了,新鲜的信息、新锐的思想扑面而来,时代的发展和进步让侯仁之为之振奋与兴奋。兴奋之余,他没忘了这次出国还要完成学校交给他的一项重大任务——应美国匹兹堡大学师生的强烈请求,为该校带去两块中国城砖。 城砖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稀罕物。上世纪60年代北京修地铁,把城墙基本上全都拆了,那些城砖有的被用去修防空洞,有的散落到民间,小胡同、大杂院里常能见到。 一番精挑细选,北京大学选定了两块带字城砖,总重近50公斤。这么重,不便携带,在那时只能海运,而海运的时间较长,一般要一两个月。正好这时候侯仁之接到匹兹堡大学的邀请,北大就请他先将两块城砖的照片和文字拓片带去,并由他代表北大赠送给对方。 侯仁之有些纳闷,两块再平常不过的城砖,为什么会引起对方那么强烈的兴趣? 到了匹兹堡大学,他被领进一间布置得很“中国”的教室,红木桌椅、高悬的孔子像,古色古香,一切元素都来自神秘的东方。原来,这所大学有18间以国家命名的教室,这间就是其中的“中国教室”。匹兹堡大学原打算将两块城砖镶嵌在这间教室的墙壁上,但知道这城砖上有字后,他们决定将城砖放在图书馆公开展览,并举行了隆重的赠送仪式。 国人视同弃物的旧砖头,却被外人视为宝物,这令侯仁之感慨、感叹,“我们还有无数更为珍贵的东西,尚未得到如此的重视与爱惜”。 两块城砖,沉甸甸地压在心头。 在美国考察期间,侯仁之结识了很多学者,接触到很多新鲜事物。1984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学时,他第一次听说国际上有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而此时,这个公约诞生已有12个年头了,但国内几乎还没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 很多外国朋友疑惑不解,中国历史那么悠久,又有着极其珍贵的文化遗址和著名的风景胜地,为什么不参加这个公约?“中国的万里长城这一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不仅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也是属于世界人民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理系斯坦伯格教授的话,犹如棒槌一样,重重地击打着侯仁之。 学者的敏感,让第一次接触“申遗”的侯仁之久久不能释怀,“这是一件大事,我国不但应当引进有利于建设物质文明的各种技术、设备和资金,而且也应该积极参加有益于世界人民精神文明的国际文化科学活动”。 回国后,侯仁之立即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了一份提案,具体介绍了有关“世界遗产公约”的情况,明确提出:“建议我国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准备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 提案写好后,侯仁之征得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三位政协委员的同意且联合签名,在1985年4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并获通过。 当年12月12日,中国终于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的缔约国。1987年12月,在世界遗产委员会第十一届全体会议上,中国的故宫博物院等6处文化和自然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999年10月29日,中国当选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成为世界上第89个加入该组织的成员国。到2005年7月,我国已拥有33项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数量位居世界第三位。 “当代中国人自应高扬中华文化的这种精神,将锦绣中华完好无缺地交到我们子孙后代的手中。” 知之愈深,爱之弥坚。 侯仁之的一生都在研究关于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学说,他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也就是他多年生活的城市——北京。为了北京,为了那些“活”着的遗产,在侯仁之温和的内心中,常常迸发出勇士的豪情。 “在卢沟河上,有一座美丽的石头桥,老实说,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把“最好”献给了卢沟桥。1937年7月7日,这座曾经“最好”的桥,目睹了侵华日军对中国军队的挑衅,也聆听了中国军人抵抗侵略的第一声枪响。那设计严谨、结构坚固的桥身,那精雕细刻、装饰着神态各异小狮子的桥栏,无不展现出古代匠人卓越的工程技术和杰出的石雕技艺。然而这座近800年历史的大桥,在上世纪80年代初,却已疲惫不堪,因常年频繁使用,未曾很好维修,桥体破损严重。 “文物古迹是城市文脉的载体,丢了它们,也就丢了城市的记忆”,侯仁之心急如焚,当即写出《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一文,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卢沟桥所面临的问题,虽然发生在首都,影响却在全国,甚至在全世界。” 文章发表在1985年8月15日的报纸上,这一天正是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纪念日。 6天以后,媒体公布了北京市政府的决定:自8月24日开始,卢沟桥禁止机动车与兽力车通行。 古桥从此正式“退役”。 此后,卢沟桥不仅多次整修,还在2002年9月公布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与宛平城同时被列为旧城外的1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2005年,北京市文物局确定了7个项目作为申报世界遗产的后备名单,卢沟桥及宛平城也名列其中。 上世纪刚进入90年代,房地产开发商涌动于北京城,推土机在老城内开动了,整片整片的胡同和四合院被涂上大大的“拆”字。 侯仁之家里的信也突然多了起来。这些信多是素不相识的老百姓写给他的,大部分是向他“投诉”某地的古迹要被拆了,希望侯先生能出面阻止。也不知大家是怎么知道侯家地址的,他每天都会收到好几封这样的信,家里几乎成了“信访办”。 这时的侯仁之很忙,出国讲学、写书,还要外出考察,但即使再忙,他也都一一给予落实。能帮着协调的,就亲自联系;自己办不了的,就委托在相关部门工作的学生们做些工作,从没让一封信在他手上耽搁过。 受身体和年龄的限制,到了90岁的时候,侯先生已经难以再漂洋过海出国交流讲学,也不能去外地考察了,甚至就连骑着自行车出去转转也已经成为奢望,但他依然关注着北京城,关注着那些珍贵的历史遗产。 “新的世纪,现代化的浪潮以前所未有的深广之势席卷全球。自然生态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已成为日益紧迫和不容回避的大问题。我们中华文化素有天人合一的境界,尤其重视人与自然及社会的和谐共存。当代中国人自应高扬中华文化的这种精神,将锦绣中华完好无缺地交到我们子孙后代的手中。”侯仁之充满深情地说。 岁月不饶人,后来时刻受病痛折磨的侯仁之常常喟叹,这几年工作得太少。“我真的那么好吗?”当荣誉、敬重和成就一一赋予他时,他常常这样自问。 他说,他只是个平凡的人,这一切都是他应该做的。 今天,当我们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吊唁这位老人的时候,又想起了他在24岁时给同学的赠言:“这件工作就是我的事业,就是我生活的重心。为这件工作,我可以忍饥、可以耐寒、可以吃苦、可以受折磨。而忍饥耐寒吃苦和受折磨的最终结果,却愈发使我觉得工作之可贵、可爱,可以寄托生命。”
|